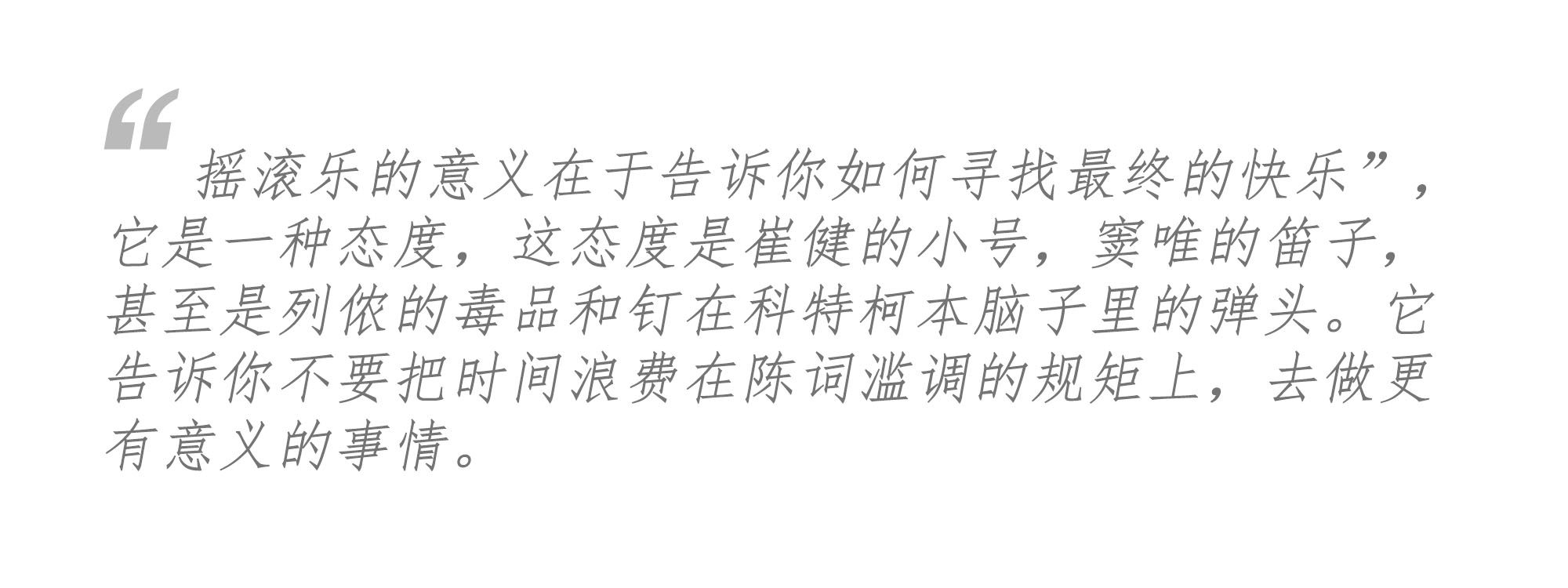一
周一上班,北京的地铁里一股子人肉味,车厢里满满当当的“沙丁鱼”,我被挤到了车厢角落,由不得我任何的反抗和挣扎,这景象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惊喜。
被挤到我旁边的是一个小个子男生,戴着耳机,可能是耳机质量不太好,我能很清楚的听到他在听什么——《陈胜吴广》,超载乐队的歌。
“还有人能听这个歌啊…”我以为除了在我的播放器里,再也不可能听到高旗了。
二
摇滚乐,说起来算是我对音乐的最初认识,上初中那会儿,周杰伦火遍大街小巷,到处都是《七里香》,唯独我抱着一盘黑豹的磁带,《无地自容》单曲循环。
后来,我听了唐朝,一首《国际歌》让我爱上了摇滚,“国际歌还能这么唱?!”起了一身鸡皮疙瘩……
再后来,我听了窦唯,听了张楚,听了子曰秋野,听了老崔,以至于后来我的歌单里只有上世纪的摇滚了……
我的歌单已经快10年没有更新过了,我甚至不用看列表就知道那些歌曲的顺序和时长,身边的朋友并不理解这种行为,更多的人喜欢听Metallica,听林肯,听GNR,说起摇滚乐,更多时候,其实是我自娱自乐,比如现在。
三
中国摇滚,摇了二十年,曾经振臂一呼万人空巷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,成了旧照片。
当年崔健用一块红布,“蒙住了双眼也蒙住了天”,窦唯梳着辫子,唱“不要纠缠我”,张楚哭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”,何勇骂“有没有希望”……每个人都把自己按在浪潮里挣扎。
后来“张楚死了,何勇疯了,窦唯成了仙”,那时的魔岩三杰,94年的香港红磡,回忆起来不光是激动,还有凄楚。当热血开始冷却,理想开始幻灭,摇滚已然走投无路了。
四
很多人并不理解,摇滚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符号。我喜欢摇滚的前十年也不理解,直到偶尔看到一部纪录片,随处飘荡的《一无所有》和摇滚版的国际歌,就像一块碑,刻着激情、无畏和热情,我瞬间理解了摇滚的真正含义,以致于我现在听到那首纪念张炬的《礼物》时,依然会被感动的一塌糊涂。
“摇滚乐的意义在于告诉你如何寻找最终的快乐”,它是一种态度,这态度是崔健的小号,窦唯的笛子,甚至是列侬的毒品和钉在科特柯本脑子里的弹头。它告诉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陈词滥调的规矩上,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
五
很多人说“中国摇滚已死”,而我并不认同,摇滚正在以另一种姿态重新回归,窦唯的《殃金咒》,就是给这个娱乐至死时代的一记沉重耳光。
摇滚,远比想象中更加暴戾,它比世俗更加黑暗,更加真实,更加不留情面。它从不温柔,也从不服从管教,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
我经常会想,如果不是那年,如果不是崔健那首靡靡之音的《南泥湾》,中国摇滚一定会比现在更辉煌,不至于20年后的今天,人们谈起摇滚依然是《梦回唐朝》和《高级动物》。
今天,我在除我之外的另一个人那里又听到了《陈胜吴广》,中国的摇滚曾经也让世界人惊呼过。我只希望,在未来的未来,我们谈起摇滚,不要只记得崔健、许巍、魔岩三杰,不要只记得20世纪八十年代,不要只记得郑钧王勇高旗丁武……我们还应该有其他响当当的名字,以及群情激奋,以及呐喊张狂……